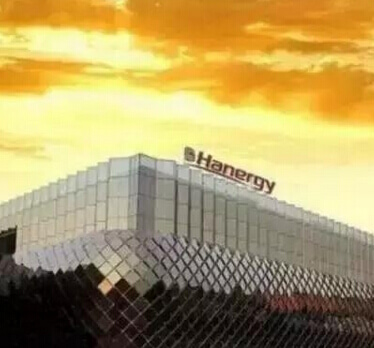鋰電世界 從演講臺走下來,華爾街大佬安德森在眾人的簇擁下緩慢地挪到了大廳門口,一個箭步鉆進了電梯。在自己的房間里,他的心腹告訴他,競爭對手又有了動作。安德森沉默了一會兒,隨后轉身凝視著鏡子里的自己緩慢而低沉地從嘴里擠出了幾個字,“這將是我的時代。”那是1994年,《華爾街金錢夢》上演。
還是那一年,李河君成立了漢能控股集團(下稱“漢能”)。
21年后的今天,李河君已經以超過1600億元人民幣的身家,成為媒體眼中擊敗馬云和王健林的中國內地“新首富”,新能源圈中的“改革派”,更重要的是,他做成了國家能源局原局長張國寶曾經“不相信”的項目。
不過,財富帶來的不僅有榮耀,還有質疑。此時的李河君在公眾面前似乎存在著兩張“面孔”:一張是媒體眼中質疑其巨額財富背后是漢能薄膜發電過度依賴母公司,存在激進擴張的“狂人”;另一張就像安德森凝視鏡中自己時所說的“這將是我的時代”。
記者見到的更像是第二張“面孔”。
“我不怕任何質疑”
1月27日,一個“新首富”誕生了。當日,漢能薄膜發電(00566.HK)上漲10.36%,報收3.73港元。在這前一天,漢能薄膜發電上漲13%。得益于漢能薄膜發電股價的上漲,加上水電、地產等非上市公司資產,漢能薄膜發電大股東李河君的身家已超過1600億元,取代馬云和王健林成為中國內地“新首富”。
2月4日,《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如約前往漢能大本營與“新首富”面對面專訪。
北京市朝陽區奧林匹克森林公園內,兩棟總面積達2.2萬平方米的多層建筑便是漢能總部,漢能是唯一落戶其中的公司。據稱,該區域是北京空氣質量最好的地方之一。
在李河君的辦公室里,雕工考究的中式家具和一幅選自秦末黃石公《素書》中語句的書法頗引人注意,偌大的書架上塞滿各種書籍,如果不是墻上“漢能司訓”的板報,這里看上去更像一間學者的書房。
盡管李河君對“首富”的報道只是淡淡回應,“我不知道哪來的,不用太當真”。而有意無意間,“首富”身份還是為其一直振臂高呼的“薄膜發電”,做了次效果極佳的傳播。
越來越多的尋常百姓由此認識了光伏,知曉了一種被統稱為“薄膜”,具有輕柔特質的可發電組件,能夠應用在建筑上、汽車上、帳篷上、手機上,甚至是服裝上,為人們提供可移動的清潔能源。
不過,在中國光伏界,由于堅定擁護“小眾”的薄膜路線,漢能總是顯得有點“另類”;李河君“把晶硅比作臺式機,將薄膜比作筆記本”的言論,更是不經意間“得罪”了絕大多數選擇晶硅路線的光伏同行。
在這場由來已久的關于“光伏技術哪家強”的爭論中,李河君堅稱,“薄膜”因具有輕柔的特質,相較晶硅產品的應用市場更為廣闊;而代表晶硅路線的一方則駁斥,薄膜的性價比無法與晶硅媲美,晶硅才是光伏“王道”。
漢能薄膜發電的股票讓李河君一躍成“首富”,而他之所以敢巨額投資薄膜發電產業,底氣就源于那座金沙江上的金安橋水電站。他說:“水電站就是印鈔機,年年有幾十億現金流。”
記者觀察到,處女座的李河君特點很明顯,頭腦清晰、對事追求完美。他并不關注“首富”這個新名號,對外界質疑其在澳門“豪賭”的新聞更是嗤之以鼻。“我不怕任何質疑,但更希望外界能夠客觀地關注漢能是一家什么企業。”
“金安橋水電站每天凈現金超1000萬”
坐落于云南金沙江中游河段的金安橋水電站,壩頂長640米,最高處達160米落差,任何立足于壩上之人都會萌生螻蟻之感,這是“西電東送”戰略目標的骨干電站之一,也是全球最大的由民企投建的水電站。
如今,當李河君再次回想起那段往事時,已經坦然。“我就是個甩手掌柜,我的管理理念就是要相信別人,讓別人做。外界都知道金安橋水電站我投了200多億,花了8年時間,但我總共去了6趟,還有兩趟是陪領導去的。”李河君坦言。
作為土生土長的客家人,李河君自小生活在廣東河源觀堂鎮一個祠堂老宅中,兄妹七人,他排行老四,小時候的李河君“話不多,但聰明、孝順”。雖上有兄長,但李河君自小跟父親關系親密,“父親是對我影響最大的人。”李河君稱。
1991年,李河君從自己的一位大學老師那里借了5萬元開始下海創業。和中國那時候許多生意人一樣,李河君“無所不做”,從賣玩具、賣礦泉水、鐵路運輸到開礦、炒地產。到1994年底,他便積累了七八千萬元的資本。
在完成了原始積累后,李河君開始考慮下一步的發展。在一位老同學的建議下,他最終決定去收購水電站。此后,李河君開始在全國尋找水電站資源。他收購的第一個水電站在他的家鄉河源——東江上一個初始裝機量1500千瓦的小水電站,花費1000多萬元。
上世紀90年代正逢中國小水電站大發展的時代。不到10年間,數萬座的小水電站在中國各地的江河上建成,其中大部分是民營水電。無疑,李河君抓住了這個機遇。
之后,李河君還收購了幾家水電站,裝機容量從幾萬千瓦到幾十萬千瓦。但真正讓李河君觸動的是2002年在云南的一次考察。這次考察過后,李河君決定押注金沙江水電站,一舉與云南省簽下了8座水電站中的6座,總裝機規模達2300多萬千瓦,超過三峽水電站。
但這個龐大的水電計劃并不順利。由于當時的國家發改委不同意,李河君無法實施這個龐大的計劃。為此,李河君一度將國家發改委告上法庭。
“坦率地講,漢能那時候告政府是不得已而為之,我們當時拿了6個水電站,國家發改委準備把水電站都拿給國有企業,一個不留給我們,做得很絕,把我逼急了。當時張國寶副主任就是不信(我們的項目能做成),說你怎么可能干得了,肯定里面有什么貓膩。他不信你,所以就要全部拿走。我們辛苦那么多年,全都給拿走,一個不給我們,我們也急了。”
當時,張國寶時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他歷來被視為穩健的官員。站在國家發改委和張國寶的角度來看,不同意有足夠的理由——特大型水電站所耗費、統籌的資源,僅庫區移民一項,金安橋水電站就涉及永勝縣3個鄉鎮7個村委會17個村組。這對一家民營企業來說是不可想象的。
最終漢能拿到了金沙江上“一庫八級”中資源最好的一座水電站,即總裝機容量300萬千瓦的金安橋水電站。
此后的8年,李河君把幾乎所有精力都花在了金安橋水電站上,累計投資超過200億元。2011年3月,金安橋水電站一期240萬千瓦機組并網發電。這也就意味著漢能未來將擁有源源不斷的資金。
在漢能的介紹中,金安橋水電站每天的凈現金流超過1000萬元,“如果按現在很多水電站2萬元/千瓦的裝機容量來算,金安橋電站價值600億元。”
正是有金安橋這棵“搖錢樹”,才使得李河君在發展薄膜的道路上底氣十足。
漢能的成功和發展,逐漸贏得了外界的認可,國家能源局原局長張國寶對李河君的態度也慢慢發生了變化。 “現在國寶主任對我們很支持,覺得真是干起來了。”李河君如是說。
轉型費用:預算150億,實際花費400多億
在完成了金安橋這個百萬千瓦級水電站后,李河君開始思考漢能的下一個方向。
事實上,在一開始,李河君并不看好光伏。在2006年時,太陽能光伏發電的成本大約是每度電3元錢。在他看來,光伏發電的成本如此之高,不可能具有競爭力。此外,根據當時的一些預測,光伏每度電的成本從3元降到1元,大約需要30年;而從1元降到0.5元,則需要50年。
但之后的現實情況讓李河君改變了看法。從2006年到2009年,僅3年時間,光伏度電成本便由3元降到了1元。
最終,李河君決定把精力放在光伏上。但令人意外的是,李河君并沒有進入技術、市場都更加成熟的晶硅技術,而是選擇了技術難度更高、資金需求更大的薄膜技術。
一直以來,在光伏領域都存在兩條技術路線——薄膜和晶硅。究竟哪種技術路線更有優勢?業內一直有截然不同的兩種看法,爭論的焦點就是成本和轉化率。在2009年,相比晶硅,薄膜并沒有多大優勢,相反,由于生產成本高,技術難度大,市場普及率差,行業并不看好。
然而,李河君作為光伏行業的后來者,卻選擇大多數同行都不做的薄膜,那時甚至有評論戲謔,“要么是瘋了!要么就是騙人!”
李河君直言:“薄膜轉化率低以及成本高是三四年前的事,現在的薄膜轉化率已經完全超過晶硅。同時,薄膜的成本已經比晶硅低。”
2009年,被認為是漢能的轉型升級之年。當年,李河君拋出了一個龐大的發展計劃,即用兩年時間上馬2吉瓦[功率單位:1吉瓦(GW)是10億瓦]薄膜產能,做到全球第一。當時,全球唯一在光伏薄膜領域有所斬獲的是美國第一太陽能(First Solar),其產能剛剛達到1吉瓦,并且已經發展了10年。
回想起當時的轉型,李河君感觸頗深。“漢能轉型是從2009年開始一直持續到2014年,剛開始的時候,我估計轉型需要花費150億,但實際上花費了400多億。漢能在轉型中選擇了薄膜發電,而當年根本沒有多少人知道究竟什么是薄膜,銀行更不會給企業貸款,這種情況下只有靠自己。”
此后,李河君經常在公開場合大力推廣薄膜技術。李河君的高調,也為他招來了不少的爭議。但就在爭議和質疑中,漢能在隨后的兩年里,成功布局了九大光伏制造基地,每個基地的起始設計產能都在250兆瓦以上。
漢能全太陽能汽車:預計10月份出樣本
除了建造基地外,李河君還努力完善從上游光伏電池和組件的生產線裝備,到中游電池、組件生產,再到下游光伏產品應用的產業鏈。
2011年,李河君通過資本市場的運作,成為在香港上市的硅基薄膜太陽能設備制造商鉑陽太陽能(00566.HK)的實際控制人,從而直入上游裝備制造。
在過去的一年中,漢能已先后與宜家、特斯拉、國際汽聯電動方程式世錦賽、阿斯頓馬丁、美麗家園等不同領域的企業跨界合作,將柔性薄膜發電技術應用于汽車、帳篷、背包、手機,甚至是衣服上,讓薄膜產品真正走進了千家萬戶。
事實也是如此,繼雷軍、賈躍亭、郭臺銘等外行“追風”進軍汽車產業外,李河君也將一只腳踏入了汽車產業。據漢能集團2月2日宣布,漢能正在研發全太陽能動力汽車,預計今年10月拿出樣車。
據李河君介紹,這一想法來自他和吉利汽車董事長李書福的一次長談。2012年,習近平總書記帶領一行企業家訪問金磚五國,李河君在隨行之列,從南非開普敦回香港的飛機上,李河君恰好與李書福坐在一起,10多個小時的飛行,他們談得最多的就是電動汽車。通過李書福的介紹,李河君意識到驅動一輛汽車走80到100公里只需要10度電,而漢能的光伏薄膜覆蓋車身可以形成一個2kW~3kW的太陽能發電系統,那么如果將6平米高效砷化鎵柔性薄膜電池集成于車身上,在日均4小時光照下,就可以驅動一輛一噸的汽車正常行駛80~100公里。兩人當下決定立馬合作開發太陽能動力汽車。
對于下一步,李河君的目標是建立吉瓦級產能的銅銦鎵硒國產化生產線,而遠期目標是到2020年打造兩個世界500強企業。
對話“新首富”:未來哪個行業最賺錢?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劉永剛采訪漢能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李河君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肖翊 攝
轉型升級概念在很多民營企業看來都很時髦,但是千萬不要亂嘗試,因為轉不好,失敗的概率很大。——李河君
《中國經濟周刊》:在你看來,未來最賺錢的行業是什么?
李河君:我覺得最掙錢的行業就在新能源領域,因為它要大量地替代傳統能源。其實漢能最大的優勢不僅僅在技術,還在于踩這個點的方向,因為企業發展最重要應該是順勢而為,沒有人能夠逆勢而做,漢能非常幸運的是已經上了軌道,所以我認為這個行業很掙錢,事實上證明確實是這樣。
《中國經濟周刊》:外媒說漢能薄膜發電過度依賴于集團公司,然后有一點激進擴張,因為它所有的營收都來自于賣設備,你怎么看?
李河君:我是這樣看的,前兩年,因為沒有人知道什么叫太陽能薄膜,所以它的銷售很困難。那時,只有漢能知道薄膜具有巨大的發展前景,我們通過買入設備扶持了上市公司。漢能作為母公司如果不把業務給自己的“孩子”,就像父母如果不在孩子困難時支持自己的孩子,孩子就會很困難。但是現在漢能的“孩子”已經長大了,會漸漸離開父母的羽翼。我們在2015、2016年將會有重大突破,只是現在還不能說。
這個行業因為是高科技加能源雙重屬性,首先高科技屬性大家非常好理解,漢能收購了很多高科技企業,但它又是能源。至于雙重屬性具體表現在什么呢?一方面有很強的技術,但同時因為能源屬性要投很多錢,這個雙門檻難度非常非常大,不是一般企業干得了的,沒有強有力的產業基礎是不行的。大家看到了600多萬千瓦的水電裝機沒有企業干得了,難度非常非常大。其實中國很多企業包括外國很多企業做薄膜的都倒下了,沒人敢干,因為這個行業太難做了,沒有產業做不起來,但是一旦做起來,大家看到市場會給出最有力的回答,剛剛做起來就會有答案。
《中國經濟周刊》:對于一家民營企業來說,如何進行轉型升級?有何風險?
李河君:現在全國各地都在說,產業要轉型、升級,我就在思考,誰是轉型升級的主體呢?我認為轉型升級的主體就是民營企業。民企轉了,則全局就轉了;民企升級了,則全國就升級了。因此要采取各種手段給民企、特別是中小企業留出市場空間,在扶持民企的政策上,要特別注意在創建中小銀行或金融機構問題上有新突破。比如美國有8000多家中小銀行,這方面,我們國家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對于漢能來說,最值得驕傲的地方是成功實現了轉型升級。我們以前是做水電、風電的,那時候我們只有幾百人。漢能在轉型過程當中選擇了薄膜發電,今年年底,漢能的員工總數將達到25000人。現在國家的轉型升級概念在很多民營企業看來都很時髦,但是千萬不要亂嘗試,因為轉不好,失敗的概率很大,其實有的企業非常好,不需要再趕那個時髦。